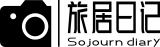NBA直播,足球直播,篮球直播,欧洲杯直播,lol直播,英雄联盟直播,dota2直播,dnf直播,cf直播,绝地求生直播,王者荣耀直播,游戏直播,赛事直播,YY直播,美女直播,视频直播,足球直播

《【复仇夜的第七章】》中的人物炎昊辰毅峰拥有超高的人收获不少粉作为一部男生生“炎昊辰”创作的内容还是有趣不做以下是《【复仇夜的第七章】》内容概括:男女主角分别是毅峰的男生生活,破镜重圆,婚恋,白月光,虐文,爽文,现代小说《复仇-夜的第七章由新锐作家“炎昊辰”所故事情节跌宕起充满了悬念和惊本站阅读体验极欢迎大家阅读!本书共计305021章更新日期为2026-01-09 01:08:34。该作品目前在本完小说详情介绍:复仇-夜的第七章
第一章 雨夜幽灵雨下得像天漏了,砸在芭蕉叶上噼啪作响。陈老太捏着手电筒,
可她心里揣着团火——武春朋家那对混账夫妻,今晚要卖孩子!“造孽啊……”她喘着粗气,
半耳朵——听到“五百块买断”“雨夜好抱娃离开”这些话——陈老太感觉心里的血都凉了。
六十多岁的人,腰杆仍挺得像标枪。抗美援朝战场上挨过弹片,上甘岭的死人堆里爬出来,
东勒村四十年没谁敢在他眼皮底下作恶。“你回去叫人,我先去拦住!”李乾威一挥手,
她看见村长从腰间抽出那根随身四十年的马鞭——牛皮浸桐油,鞭梢嵌着块弹片,
抽下去能揭人一层皮。武家破屋里,煤油灯晃得人影鬼祟。“老曹,五百太少了。
”邱仑枝缩在炕角,怀里抱着个襁褓。孩子才半岁,瘦得只剩把骨头,哭都哭不出声。
烟雾混着霉味:“再加一百,六顺。”“成!”花衬衫爽快掏钱,“雨大,我们得赶紧走。
”就在他伸手接孩子的刹那——“砰!”木门被一脚踹开,雨水裹着寒气灌进来。
李乾威站在门口,浑身湿透,眼睛却亮得骇人:“武春朋,你找死!”屋里三人全僵住了。
花衬衫反应最快,抱起孩子就往里屋窜。同行的女人反应也不慢,迅速拉开后窗:“曹哥,
跳!”“放下孩子!”李乾威鞭子一甩,啪地抽在花衬衫背上。衣服裂开道血口子,
花衬衫的曹姓男子惨叫一声,迅速把孩子往女人手里一塞:“快跑!”女人接住襁褓,
翻身出窗。花衬衫转身抄起条凳砸向村长,趁格挡的间隙也翻了出去。李乾威没追,
鞭子指向武春朋:“你,还有你婆娘,现在去把孩子追回来!追不回来,我打断你们的腿!
”老村长一声暴喝,屋梁都在震武春朋腿一软,竟跪下了:“村、村长,他们往山里跑了,
手电光在泥泞山路上乱晃,村里青壮陆续追出来。李乾威跑在最前头,六十七岁的年纪,
脚步却比小伙子还稳。“村长!那边!”有人喊。山道拐弯处,隐约见两个人影。
抱孩子的女人脚下一滑,摔进路边沟里。花衬衫去拉,手电光已逼近。“曹大狗,
声音却被雷声吞没。电光撕裂夜空那一瞬,他看见武春朋和邱仑枝正偷偷往村外溜。
怒火攻心,他拔腿要追,脚下却踩中一片松动的石板——“咔嚓!”路面塌下去一块,
李乾威护着孩子整个人失去平衡向后一仰,后脑重重磕在凸起的岩石上,闷响混在雨声里,
轻得没人听见。手电滚落,光柱扫过他睁大的眼睛。血从白发间渗出,迅速被雨水冲淡,
手臂还保持着环抱的姿势,像护着什么稀世珍宝。襁褓里,婴儿的啼哭撕心裂肺。
”老赤脚医生探了鼻息,摇头,“半个钟头前就走了。”雨还在下,砸在每个人脸上,
露出孩子手腕——那里系着根红绳,栓着枚磨亮的弹壳。是村长从朝鲜带回来的,说能辟邪。
李乾威无儿无女,棺材前却堆满供品——他救过的人太多了。陈老太抱着孩子跪在棺侧,
旁边是她老伴炎国富。老爷子五十九岁,村里唯一的秀才,此刻佝偻着背,老泪纵横。
武老太领着几个儿女挤进来,三角眼扫过灵堂,径直走到炎国富面前:“炎老哥,
听说你要收养小宝?”炎国富抬头,目光冷下来:“是。”“那敢情好。”武老太咧嘴笑,
露出豁牙,“不过咱得把话说清楚——这孩子我们武家不要了。他爹妈跑了,我们是养不起,
字据我都带来了。”她从怀里掏出张皱巴巴的纸,上面按着几个红手印。祠堂里顿时炸了。
”武老太叉腰骂回去:“嚷嚷什么?一节竹子不关二节事!我带大三儿两女够苦了,
还想让我带这祸胎?没门!”炎国富盯着那张纸,手指关节捏得发白。许久,他接过笔,
在收养人那栏签下名字。“从今往后,孩子姓炎。”他一字一顿,“叫炎毅峰。毅力的毅,
山峰的峰——村长取的名,我替他落定。”武老太哼了声,扭身就走。路过陈老太身边时,
孩子小手抓住爷爷花白的头发,咯咯地笑。“那是稻子。”炎国富指着田,“春种秋收,
他教过三个女儿,教过村里娃娃识字,从没像现在这样,把一个词反复念出甜味。
陈家没有男丁。三个女儿出嫁时,陈老太偷偷哭了好几夜。现在灶台边总温着米糊,
摇篮里总有奶香,她皱纹都舒展开,走路带着风。“咱小宝有福相。”她给毅峰缝虎头帽,
针脚密实,“你看这额头,多宽。村长取的名好,毅峰,像山一样。”孩子满周岁那天,
老人抱着毅峰在画像前磕头。“乾威兄,孩子周岁了。”炎国富声音发哽,“你放心,
像他们从未存在过。二、裂痕平静在毅峰五岁那年碎了。那天他在村口老槐树下玩石子。
几个稍大的孩子围过来,领头的是武老太的大孙子武强,8岁,壮得像小牛犊。“喂,野种。
眼神干净:“这儿是大家玩的地方。”“大家?”武强咧嘴笑,“你算哪门子大家?
你爹妈是人贩子,把你卖了换白面吃!”孩子们哄笑。毅峰站起来,小手攥紧:“我有爷爷,
有奶奶。”“那是假的!”武强凑近,压低声音,“你知道李爷爷怎么死的吗?就因为你!
你要是不被生出来,李爷爷现在还活着!”炎毅峰愣住了。那些深夜里爷爷奶奶的叹息,
那些村民看他时复杂的眼神,祠堂画像上老人锐利的目光……碎片忽然拼凑出可怕的形状。
孩子一头扎进她怀里,浑身发抖。“咋了小宝?谁欺负你了?”陈老太慌得放下菜刀。
炎毅峰抬头,眼泪滚下来:“奶奶,李爷爷……是不是我害死的?”陈老太手一颤,
”“武强说……说我是祸胎。”孩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,“说我要是不被生出来,
李爷爷就……”“放屁!”灶台边传来一声闷响。炎国富把柴刀剁在案板上,脸色铁青,
“小宝你听好——李爷爷是英雄,你是英雄救下的孩子。那些嚼舌根的,心肝让狗吃了!
三、毒刺自那天起,炎毅峰变了。不再跟村里孩子玩,总是一个人蹲在田埂看蚂蚁搬家。
“这孩子心思太重。”陈老太夜里跟老伴叹气,“才五岁啊。”炎国富沉默着卷烟。
毅峰喜欢去竹林边捡竹壳,陈老太说能引火。那天他正蹲着挑,背后传来脚步声。“哟,
这不是我家小宝吗?”炎毅峰回头,血液瞬间冻住。武老太挎着篮子,三角眼笑眯眯的,
武老太笑容垮下来:“怎么,跟了姓炎的,连亲奶奶都不认了?”“我……我有奶奶。
捡个祸胎当宝。”她凑近,压低声音,“你知道你爹妈为啥不要你吗?因为你命硬,克人。
跟你那贱妈一样反骨!”她突然伸手,狠狠推在毅峰胸口。孩子往后倒,脚下是陡坡。
后脑撞上什么坚硬的东西。剧痛炸开前,他看见武老太站在坡顶,冷冷看着,然后转身走了。
竹桩从肩膀刺进去,扎得不深,但血很快洇湿衣服。毅峰张了张嘴,发不出声音。
炎家小宝出事了!”四、倾家镇医院消毒水味儿刺鼻。炎国富蹲在走廊,烟抽了一根又一根。
护士过来劝:“老爷子,这儿不能抽烟。”他像没听见。手术室门开了,医生走出来,
白大褂沾着血:“命保住了,但颅内有瘀血,压迫视神经和记忆区。得转市里做手术,
越快越好。”“多少钱?”炎国富声音干哑。医生报了个数。老人手一抖,烟灰落在鞋面上。
陈老太当场晕过去。接下来一个月,炎家天塌了。存款掏空,粮食卖了,猪杀了。
炎国富跑遍全村借钱,老脸赔尽。三个女儿凑来些,杯水车薪。最后他去信用社,
用老屋做抵押,贷了笔天文数字的款。手术做完那天,毅峰醒了。眼睛蒙着纱布,
说话慢半拍。“爷爷……”他伸手在空中摸。炎国富抓住那只小手,老泪纵横:“哎,
”其实陈老太也倒下了。打击太大,血压飙到危险值,医生说要静养,不能再受刺激。
毅峰出院时,右眼视力只剩0.2,看东西总有重影。记忆也出了问题,昨天的事今天忘,
五、遗忘回家那天,村里静得诡异。武家大门紧闭,听说武老太“走亲戚去了”。
没人提竹林的事,像那只是一场意外。但炎家已经空了。米缸见底,肉腥味成了记忆。
老人肉眼可见地衰败下去。炎国富背驼了,陈老太常坐着发呆,喊她几声才回神。有天夜里,
“我的小宝……命怎么这么苦啊……”炎国富坐在床边,一言不发,只是把老伴搂进怀里。
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,在月光下缩成小小一团。毅峰退回自己屋,爬上床,用被子蒙住头。
眼泪浸湿枕头,他咬住被角,不敢出声。第二天,陈老太忘了他是谁。“你是哪家娃娃?
”她端详毅峰,眼神陌生,“长得怪俊的。”毅峰手里的碗掉在地上,玉米糊洒了一地。
炎国富从外面回来,见状沉默许久,蹲下收拾碎片。收拾完,他把毅峰拉到灶房,
”可毅峰看见爷爷眼底的绝望。几天后,炎国富也开始忘事。喊错女儿名字,出门忘了锁,
有次烧火差点把灶房点着。毅峰成了这个家唯一清醒的人。六岁的孩子,学做饭,学喂鸡,
学给爷爷奶奶洗脸擦身。村里人看不过去,轮流送些吃的,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
六、抉择深秋的早晨,霜打枯草。毅峰把最后半碗米熬成粥,喂爷爷奶奶吃完,收拾了碗筷。
然后他回到自己屋,从床底拖出个破书包——是陈老太用旧衣服改的,针脚歪斜,但很结实。
往里装了两件换洗衣服,一小袋炒米,还有那个弹壳。红绳已经褪色,弹壳磨得锃亮。
桌子纸本上留了一行字“小妈妈,我走了,不用找我,你们照顾好爷爷奶奶,炎毅峰!”,
昨天他跟小“妈妈”说今天中午有事找她。毅峰叫老头老太太的小女儿“小妈妈”!
他在爷爷奶奶床前跪下,磕了三个头。“爷爷,奶奶,小宝走了。”他声音很轻,
他又去了祠堂。李乾威的画像蒙了尘,他踮脚擦干净,跪下又磕三个头。“李爷爷,对不起。
”他哽咽,“等我长大了,一定做个像您一样的人。”最后他来到村口老槐树下。晨雾未散,
村子还在沉睡。他回头看了一眼——陈老太的烟囱没冒烟,炎国富的咳嗽声没传来。
这个养育他六年的家,正在遗忘中慢慢死去。他转身,走进浓雾。书包很轻,脚步很沉。
山路泥泞,他摔了好几跤,爬起来继续走。走到镇子时天黑了,花五分钱买了两个馒头,
”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,悠长,凄厉,像某种召唤。毅峰站起来,朝声音方向走去。
瘦小的身影逐渐融入夜色,像一滴水汇入黑色的海。而东勒村的清晨,和往常一样来临。
鸡鸣,狗吠,炊烟升起。没人注意到,那个总在田埂看蚂蚁的孩子,已经消失在晨雾深处。
---第三章 白月光一、砖窑县城的柏油路烫脚。炎毅峰蹲在路边,看汽车扬起尘土。
他离开村子七天了,身上二十块钱变成五个馒头、三碗稀饭,还有此刻肚子里空荡荡的回响。
“小孩,找不着家了?”声音从头顶传来。是个老太太,蓝底花布衫,笑眯眯的,
手里提着菜篮子。毅峰站起来,拍拍裤子上的灰:“我……我没家了。”“哎哟,造孽。
”老太太蹲下,掏出手绢给他擦脸,“跟婆婆走,婆婆那儿有吃的。”她的手很软,
有股肥皂香。毅峰想起陈老太给他洗脸的样子,鼻子一酸。“真的?”“真的,婆婆不骗人。
”老太太牵起他的手。手很暖,毅峰跟着走,穿过两条街,拐进条巷子。巷子尽头有扇铁门,
生着锈,推开时吱呀响。院里站着个光头男人,胳膊上纹条青龙。“刘婶,又捡一个?
”男人打量毅峰,“啧,太小了,干不了活。”“养养就大了。”刘婶推毅峰上前,
“包吃住,不要工钱。”男人捏起毅峰下巴,看了看牙口:“行吧,先扔窑里练练。
”后来毅峰才知道,这叫黑砖厂。进去的,没几个能出来。砖窑像怪兽的嘴,日夜冒黑烟。
六岁的孩子,搬不动整砖,就搬半砖。砖还烫着,手很快磨出血泡,血泡破了,结成茧,
第二天就换张新面孔。毅峰不哭。他把弹壳穿根绳挂脖子上,贴着心口。烫砖时烫着手,
他就摸摸弹壳。李爷爷说这能辟邪,他想,邪大概就是窑里这些拿鞭子的人。一个月后,
他看见第一个死人。是个四川来的大叔,连着干了三天夜班,早上换班时一头栽进砖堆。
监工过来踢两脚,骂了句“晦气”,叫人拖走。“拖哪儿去?”毅峰小声问旁边老伯。
老伯眼神麻木:“还能哪儿,火窑里一扔,烧成灰,混进砖里。”那天夜里毅峰做噩梦,
梦见自己也变成砖,砌进墙里,墙越砌越高,把他封在黑暗深处。二、微光砖厂在雨季出事。
听见外面乱糟糟喊:“警察来了!快跑!”窑工们愣了几秒,然后疯了似的往外冲。
监工举着铁棍拦,被人潮撞翻。毅峰跟着跑,雨浇在身上,冷得打颤,心里却有团火在烧。
厂门口停着几辆警车,灯闪得刺眼。穿制服的人拿着喇叭喊:“都别慌!排队登记!
端这黑窝……”“地头蛇早跑了,活该!”登记完,警察说可以安排回家。轮到毅峰,
他摇头:“我没家。”女警察蹲下来,眼睛很温柔:“那你亲戚呢?”“都死了。
”女警察沉默片刻,从兜里掏出一百块钱:“先去吃点东西,明天去救助站。”毅峰捏着钱,
没走。他在雨里站了很久,看窑工们陆续被车接走。最后剩下三个半大孩子,你看我我看你。
爹妈赌钱跑路了。”最后轮到毅峰。他嗓子发紧,半天才憋出句:“炎毅峰,六岁。
爸爸妈妈……不要我了。”王全咧嘴笑,露出一口黄牙:“行,咱们仨,凑一伙。
”三、桥洞王全是湖。他带两人摸到县城中学后墙,扒开杂草,露出个半人高的桥洞。
“我地盘。”他得意地拍拍胸脯,“冬暖夏凉,还没人抢。”洞里铺着旧报纸,有股霉味。
”所谓“开荤”,是翻餐馆后门的泔水桶。王全有经验,专挑晚上八九点去,那会儿刚打烊,
他嚼着沾满油污的馒头,想起陈老太做的玉米饼,金黄金黄的,上面撒芝麻。“想啥呢?
”王全哼了声:“有得吃就不错了。这世道,活下来是本事,别的都扯淡。”夜里下起雨,
桥洞漏雨,三人缩在干处。叶仟忽然说:“咱们拜把子吧。以后有福同享,有难同当。
”没香,折三根草棍插在泥里。王全最大,是大哥;叶仟老二;毅峰老三。磕完头,
王全说:“以后谁混出头了,得拉另外两个一把。”“一定。”毅峰认真点头。他那时真信,
信兄弟,信义气,信人在做天在看。四、裂痕流浪五年后,转机来了。一家小餐馆招杂工,
最后一家比较忙碌的米线店要了叶仟去后厨洗碗,3毛钱一天,还可以下班带些剩饭菜!
但晚上能带回几个馒头、一些剩菜。三人分着吃,桥洞里第一次有了笑声。可裂痕来得也快。
上班几个月后,王全渐渐不出现了。叶仟去找他,回来时脸色难看。“他说啥了?”毅峰问。
叶仟憋半天,吐出句话:“他说……跟我们混,丢人。”那晚桥洞特别冷。毅峰抱着膝盖,
看洞外路灯昏黄的光。弹壳在心口发烫,他想,是不是自己真的不吉利,谁沾上谁倒霉?
有一天,毅峰在路上碰到王全。“以后别来找我了。”王全穿着新买的夹克,头发抹了发油,
“我有正经工作了,你们……好自为之。”“可我们是兄弟。”毅峰声音发颤。“兄弟?
”王全笑了,笑得很难看,“这世道,兄弟值几个钱?看到你们,我就想起翻垃圾桶的日子。
我受够了。”他转身走了,没回头。五、兄弟别王全走后,叶仟成了毅峰唯一的依靠。
但叶仟说:“等哥攒够钱,租个房子,咱也像个人样。”毅峰信他。叶仟眼睛亮,说话算数。
变故发生在一个雨天。叶仟下班回来,脸肿着,嘴角有血。“咋了?”“碰见武强了。
”叶仟啐了口血沫,“就是当年骂你祸胎那小子。他跟几个混混在县城混,认出我,
说我是你同伙。”毅峰血往头上涌:“我去找他们——”“回来!”叶仟拽住他,
“他们四个人,你找死啊?”他从怀里掏出个布包,层层打开,里面是皱巴巴的纸币,
“我攒的,六十块。你拿着,找个地方先躲躲。”“那你呢?”“我?”叶仟咧嘴笑,
扯到伤口嘶了声,“我去找他们算账。放心,哥有办法。”那天晚上,叶仟走了再没回来。
信上字歪歪扭扭:峰娃:哥把那四个杂种打了,钱抢回来了。这一百你拿着先用。
我得离开一阵,别找我,等风头过了哥回来找你。记住,好好活。你仟哥---信纸上有血,
但他觉得心里空了一大块。六、遇见遇见陈纤那天,毅峰正打算去死。叶仟消失半个月了。
毅峰寻遍县城,没有音讯。一百块钱花得很快——他租了间最便宜的房子,买了身干净衣服,
去应聘所有能看见的招工。可六岁的孩子,谁要?钱快见底时,他坐在马路牙子上,
”声音从旁边传来。是个女孩,头发乱糟糟,衣服宽大,但脸洗得很干净,眼睛像两汪清泉。
毅峰没理。“你是不是没地方去?”女孩蹲下来,和他平视,“我也没有。”毅峰这才看她。
女孩大概十岁左右,脖子很细,锁骨凸出来。“我叫陈纤,十六岁。”她说,“其实十一岁,
但报大点好找活。”“炎毅峰,十二岁。”毅峰顿了顿,“对别人报十六岁。”陈纤笑了,
陈纤带毅峰去了她的“家”——半间废弃的门卫室,用木板隔出个角落。地上铺着纸壳,
墙上贴满从垃圾堆捡来的画报。“好看吧?”她指着一幅山水画,“我选的。”毅峰点头。
他很久没见过这么用心的“家”了。陈纤煮了面——真的是煮,用捡来的小电炉,
偷接的路灯电。面是挂面,汤里飘几片菜叶,但她打了颗鸡蛋,金黄的蛋黄铺在面上。
“吃吧。”她把碗推给毅峰,“我吃过了。”毅峰知道她没吃。但他太饿了,狼吞虎咽吃完,
抬头时看见陈纤在咽口水。“明天我请你。”他说。“好啊。”陈纤眼睛弯成月牙,
“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”“什么事?”“做我朋友。”她认真地说,“我没朋友。
陈纤也“工作”——她在菜市场帮人看摊,换点菜叶子。晚上两人挤在狭小昏暗的出租屋,
一起练习认字。“这是‘家’。”她一笔一画,“上面是房子,下面是猪。有房有猪,
说完两人冲着对方龇牙大笑!陈纤长得好看,但她总把自己弄脏——脸上抹灰,头发打结,
穿宽大的旧衣服。毅峰问为什么,她说:“漂亮危险。我二姐就是太漂亮,被人拐走了。
笑着笑着掉眼泪:“傻子,你才多大。”可从那以后,她渐渐收拾自己了。洗脸,梳头,
偶尔捡到好看的发绳会戴上。晚上在灯下,她侧脸像幅画,睫毛很长,鼻梁挺翘,
毅峰常看呆。“看什么?”她瞪他。“看你好看。”毅峰实话实说。陈纤脸红了,
他说在一家技校招生,一天能挣两块,问毅峰干不干。毅峰心动。两块,能买四斤米,
够和陈纤吃好几天。他去了。确实在街边搭棚子,正经招生。干了三天,每天结钱。
第四天晚上,马银川请他吃饭,说:“把你那小妹妹也叫上,哥请客。”毅峰犹豫。
陈纤说不见生人。“怕啥?我是你哥,还能害你?”马银川搂他肩膀,“哥看你俩不容易,
想帮你们。技校包吃住,还能学手艺,你俩都能去。”毅峰心动了。他想学手艺,挣钱,
给陈纤买新衣服。那顿饭在个小馆子。马银川很会说话,逗得陈纤直笑。毅峰喝了两杯汽水,
有点晕,去厕所回来时,看见马银川往陈纤杯子里撒了点什么。“你干嘛?”毅峰冲过去。
“糖。”马银川面不改色,“妹妹爱喝甜的。”陈纤已经喝了一口,咂咂嘴:“是甜。
”毅峰狐疑,但没再问。那天晚上陈纤睡得很沉,第二天起来说头疼。毅峰担心,
马银川说:“没事,昨天累着了。今天哥带你们去技校看看。”技校在城郊,很偏。
三层旧楼,门口牌子歪着。马银川说先办手续,让陈纤在一楼等,带毅峰上三楼。“填个表。
最后听见的声音是马银川的冷笑:“小崽子,怪就怪你妹妹太水灵。”九、深渊毅峰醒来时,
在货车上。手脚被绑,嘴贴胶布。车厢里还有几个女孩,都昏睡着,陈纤在最里面,
脸色惨白。车颠簸了很久,停下时天黑了。马银川拉开车门,和另一个男人把女孩们拖下来。
卖去昆明至少五千。”“那这小子呢?”同伙踢踢毅峰。“麻烦,找个地方扔了。
”毅峰被拖到仓库后,扔进条水沟。水不深,但臭,他挣扎着坐起来,用石片磨绳子。
磨了不知道多久,绳子断了,他撕掉胶布,大口喘气。仓库里传来哭声。他爬回去,
扒着窗缝看。陈纤醒了,缩在墙角。马银川在数钱,旁边站着个穿花衬衫的男人,
正在捏陈纤的脸。“确实嫩。”花衬衫笑,“今晚我先验货。”毅峰血往头上涌。
他捡起块砖头,想冲进去,脚却像钉在地上。他想起自己六岁,想起砖厂的鞭子,
想起武强说“祸胎”。他怕。里面传来布料撕裂的声音,和陈纤的尖叫。毅峰转身跑了,
他跑得很快,像身后有鬼追。一直跑到城里,跑到出租屋,砰地关上门,缩在墙角发抖。
天亮时他回去,仓库空了。地上有滩暗红的血,旁边扔着陈纤的发绳——红色的,
她昨天刚戴上,说本命年要辟邪。毅峰捡起发绳,攥在手心,攥得指甲嵌进肉里。他没哭。
眼泪早就流干了。十、浑噩的幽灵陈纤失踪后,毅峰成了真正的幽灵。他不工作,不吃饭,
每天在县城游荡。饿了翻垃圾桶,困了睡桥洞。头发长了,衣服破了,身上有味儿,
路人躲着走。有天他撞到个人,被一脚踹倒。“臭要饭的,不长眼!”毅峰爬起来,继续走。
额头流血了,他不管。走到陈纤住过的门卫室,木板还在,纸壳还在,墙上的画报被雨打湿,
好像看见叶仟咧嘴,说“哥有办法”,好像摸到弹壳,李爷爷在雨里说“放下孩子”。
都散了。像场梦。不知躺了多久,他坐起来,从怀里掏出两样东西:弹壳,和红发绳。
用发绳把弹壳重新串好,挂回脖子上。然后他走到河边,蹲下,仔仔细细洗脸,洗手,
把头发拢到脑后。水里的倒影很陌生:脸颊凹陷,眼睛深得像个窟窿。但眼神变了。
不再有怯,不再有软,只剩一片死寂的冰。他站起来,朝县城深处走去。步子很稳,一步,
在路灯下像无数银针。毅峰没躲。他仰起脸,让雨浇在脸上。心里有个声音在说:从今天起,
---第四章 十年一、蛹昆明火车站,人流像浑浊的河。炎毅峰蹲在出站口的台阶上,
数鞋尖前的烟头。第七根时,有个穿皮夹克的男人停在他面前,影子罩住他。“小孩,
笑起来像蜈蚣在爬。“去哪?”毅峰声音沙哑。他十三了,看着像十岁,瘦得颧骨凸出来。
他在昆明找了一年,陈纤的线索断在火车站。有人说看见相似女孩被带上南下的火车,
再往后,没了。“我去。”他站起来。男人咧嘴笑,露出金牙:“聪明。”车是半夜开的,
一辆破旧面包车,塞了十二个人。毅峰缩在角落,旁边是个云南女孩,十四五岁,一直在抖。
车过边境时被查了。手电光扫进来,女孩吓得往毅峰身后躲。疤脸男人下车交涉,递烟,
塞钱,点头哈腰。几分钟后,栏杆抬起。“记住。”男人回车上,眼神阴沉,“过了这道线,
是黏糊糊的、带着香料和腐殖质气味的热。毅峰被扔进一家叫“翡翠宫”的夜总会后厨,
洗碗,从下午四点洗到凌晨四点。厨房像个蒸笼,汗流进眼睛,蜇得生疼。管事的叫坤哥,
潮汕人,手里总拎根藤条,谁慢抽谁。“大陆仔,快点!”藤条抽在背上,辣的。
坤哥忽然说:“前厅缺个送酒的,你去试试。”前厅是另一个世界。水晶灯晃眼,
香水味混着雪茄烟。女人穿得少,露着大腿和肩膀,在男人怀里笑。音乐震得地板发颤,
有人往他领口塞小费。他面无表情,眼睛像扫描仪,扫过每一张脸。陈纤不在这里。
包厢里的事更脏——毒品、肉体交易、现金一沓沓扔在桌上当筹码。毅峰学会了笑,
学会了弯腰,学会了把厌恶压进胃里,变成冰冷的石头。夜里回宿舍,八人间,上下铺。
一个词一个词啃。看不懂的记在本子上,第二天问吧台调酒师。调酒师是台湾人,
”三、第一个猎物机会来得很偶然。VIP包厢常客里有个泰国军官,叫巴颂,中校衔,
让说出酒的年份和背景,经理只知道个大概!经理只能尴尬赔笑,巴颂抬手要打。
所产红酒也为历年以来品质之最!”包厢静了。巴颂转头看他:“你懂酒?”“学过一点。
”毅峰垂着眼。他花了三个月工资,请调酒师教品酒,背产地、年份、口感特征。
巴颂松开经理,坐回沙发:“过来,说说这瓶。”毅峰走过去,倒一点,晃杯,闻,
但醒酒时间不够,再放二十分钟更好。”巴颂盯着他看了很久,忽然大笑:“小孩,
你多大了?”“十六。”毅峰撒谎。他实际十四,但个子窜得快,脸上棱角初现。“跟。
”巴颂说,“月薪五千泰铢,比你在这儿洗杯子强。”经理脸色变了:“巴颂长官,
”经理闭嘴了。毅峰放下托盘,鞠了一躬:“谢谢长官。”走出包厢时,他手心全是汗。
四、棋局巴颂的“生意”很杂:夜总会干股、地下**、走私香烟。毅峰名义上是助理,
实际是打杂兼保镖。巴颂喜欢他沉默、机灵,更重要的是——干净,没背景,好控制。
巴颂给某警察局长送了多少;某次走私,海关谁放的水;**分红,哪些官员有份。
人名、金额、时间,记在一个巴掌大的本子上,藏在内裤暗袋。晚上回到贫民窟的出租屋,
他把账誊到墙上——用铅笔写,写完用海报盖住。墙上密密麻麻,像蜘蛛网。一年后,
巴颂让他接触核心:毒品。“这批货从金三角来,你跟着去接。”巴颂拍拍他肩膀,
毅峰站在巴颂身后,看双方验货——白色粉末,用透明塑料袋装着,在月光下像砂糖。
“尝尝?”缅甸人咧嘴,露出黑牙。巴颂沾一点放舌尖:“纯度不错。”回去的路上,
巴颂开车,心情好,哼着歌。毅峰坐在副驾,忽然说:“长官,我觉得不对劲。”“怎么?
”“刚才验货时,那个缅甸人右手一直插在兜里。”毅峰说,“我瞥见,兜里有枪。
”巴颂猛踩刹车,掏出手机拨号:“货别卸!原地等着!”他派人回去查,果然,
缅甸人埋伏了枪手,想黑吃黑。因为毅峰的提醒,巴颂的人反埋伏,把对方全端了。那晚,
巴颂给毅峰倒了杯威士忌:“小子,你救我一命。”毅峰接过酒,没喝:“长官,
我想学更多。”“学什么?”“学怎么当爷,不当狗。”巴颂盯着他,很久,笑了:“有种。
怎么在法律的缝隙里建自己的王国。毅峰学得快,下手狠,到十七岁时,已能独当一面。
巴颂越来越倚重他,很多事交给他办。但毅峰知道,自己永远是条狗。巴颂高兴时赏骨头,
毅峰偷听到巴颂和心腹的对话:“那小子越来越精了,得防着。”“要不……这次做完,
处理掉?反正他知道的太多。”巴颂沉默片刻:“可惜了,是个人才。不过,不能留。
”毅峰在阴影里站了很久,直到腿麻。回屋后,他烧了那面写满账的墙。灰烬冲进马桶,
毅峰更快——他袖子里滑出把匕首,一刀捅进巴颂肋下。不是要害,但足够让他倒下。
“为什么?”巴颂瞪着眼,血从嘴里涌出来。“因为你教我的第一课:想活,就得狠。
他打量毅峰:“你就是那个提供情报的小孩?”“是。”“胆子不小。”差猜笑,
”毅峰从怀里掏出个U盘:“这里面有巴颂所有生意的账目,还有他背后十七个官员的把柄。
我用它,换一张干净的身份,和一笔启动资金。”差猜盯着U盘,笑了:“你多大?
在曼谷唐人街开了家小酒吧,叫“纤归”。招牌是汉字,红底金字。店里放邓丽君的歌,
卖绍兴黄酒、四川火锅。来的多是华人,思乡的,逃难的,做灰色生意的。毅峰亲自调酒。
他学会笑,学会聊天,学会从客人的醉话里筛出信息:谁需要洗钱,谁需要保镖,
都知道“纤归”的老板年轻,但路子野,办事牢靠。一年后,“纤归”变成三家店。
毅峰注册了公司,叫“炎黄集团”,业务拓展到物流、地产。他穿西装,打领带,
他回到顶层公寓,才会摘下所有面具。站在落地窗前,看曼谷的霓虹像流淌的血。
只有三样东西:陈纤的发绳。叶仟那封带血的信。还有一张泛黄的照片——六岁的他,
1990年夏。”他看了很久,然后锁上柜子。该开始了。七、织网复仇需要网。
毅峰的第一条线,伸向信息。他成立“信息咨询部”,名义上为企业提供市场分析,
实际养了一批私家侦探、黑客、线人。任务只有一个:找人。找陈纤,找叶仟,找马银川,
条件是他们考上大学后必须从政。他在警察、海关、移民局发展线人,用钱,也用把柄。
第三条线,伸向暴力。他从金三角招募,成立“安保公司”。这些人背景复杂,
到毅峰二十岁时,他已掌控曼谷三分之一的地下情报流,黑白两道都要给他面子。
差猜将军退休那天,请他到家里吃饭。老将军头发白了,但眼神依旧锐利。“小子,
“所以来找您,讨个护身符。”“什么护身符?”“我想做点正经生意。”毅峰说,
”差猜笑了:“你终于想洗白了。”“不是洗白。”毅峰放下茶杯,“是把黑变成灰,
灰变成白。我要站在光里,做我想做的事。”差猜盯着他,很久,点头:“我有个侄女,
在旅游局。介绍你们认识。”侄女叫诗琳通,二十八岁,留学英国回来,干练,聪明。
第一次见面,她就看穿毅峰:“你想借我搭桥,进入上层圈子。”“互惠互利。”毅峰坦率,
“你需要政绩,我需要保护伞。”诗琳通笑了:“你不像个生意人。”“那我像什么?
”“像个……复仇者。”她眨眨眼,“别否认,我看得出来。你眼里有火,烧了很多年了。
”毅峰没接话。那晚他失眠,站在窗前直到天亮。诗琳通说得对。他不是生意人,是复仇者。
所有财富、权力、人脉,都是武器。他在铸造一把刀,刀锋所指,是十年前那个雨夜,
八、第一个缺口信息部传来第一份捷报:找到马银川了。“在缅北。”负责人是个前情报官,
代号“鹰眼”,“他还在干老本行,骗女孩过去,卖到**和妓院。有个长期相好。
”毅峰看着照片。马银川老了,胖了,但那双黄鼠狼似的眼睛没变。“他父母呢?
”“在边境,贩毒为生。上个月被警察端了,老两口跑路,现在躲在勐腊。”毅峰沉默。
窗外在下雨,曼谷的雨季来了,空气黏稠得像糖浆。“抓活的。”他最后说,“一家三口,
”第二个消息接踵而至:当年抢劫他们的四个混混,找到了。“都在国内。一个在广东打工,
一个在老家开麻将馆,一个因抢劫入狱刚释放,一个……”鹰眼顿了顿,“死了,吸毒过量。
”毅峰转动椅子,面向墙上的地图。中国西南,那片他出生长大的土地,被红笔圈出几个点。
“还剩三个。”他轻声说,“请他们来泰国旅游。费用全包。”“如果他们不来?
”“那就绑。”毅峰回头,眼神平静,“记得用麻袋,别伤着脸。我要他们清醒地来,
清醒地受罪。”鹰眼点头,退出办公室。毅峰走到酒柜前,倒了杯威士忌。没喝,
只是晃着杯子,看琥珀色的液体挂壁。快了。他仰头喝干,烈酒烧喉,像吞下一把火。
九、归途二十二岁那年,毅峰第一次回国。以“泰籍华商”身份,投资考察团成员。
飞机落地昆明,他走出舱门,深吸一口气——空气里有灰尘和植物的味道,和曼谷不一样。
他蹲在当年蹲过的台阶,抽了根烟。有个中年女人过来,像当年疤脸男人一样问:“小弟,
找工作吗?”毅峰抬头看她。女人四十多岁,皱纹很深,眼神麻木。“我找个人。”他说,
“大概十年前,在这儿被拐走的女孩,叫陈纤。眼睛很大,左边眉毛有颗痣。”女人愣了下,
眼神闪烁:“没、没见过。”毅峰从钱包抽出一沓钱:“真没见过?”女人盯着钱,
吞口水:“真没有……不过,十年前确实有一批女孩被弄到泰国,我听说,有个特别漂亮的,
被卖去曼谷的夜总会,叫什么……‘金凤凰’。”金凤凰。毅峰手一颤,烟掉了。
那是曼谷最高档的夜总会之一,他常去应酬,从没想过陈纤可能就在那里。“谢谢。
”他把钱塞给女人,转身就走。回酒店路上,他给鹰眼打电话:“查‘金凤凰’,
老板是军方的人。”“查。”毅峰一字一顿,“用一切手段。”挂断电话,他靠在后座,
十、暗涌考察团最后一站,是毅峰的“家乡”。车队开进县城时,他摇下车窗。街道宽了,
中学门口卖文具的老太太。他在炎家老屋前下车。房子还在,但院墙塌了半边,门锁锈死。
”“我……”毅峰顿了顿,“我是他们远房亲戚。”“哦。”邻居指指巷子深处,
“不过武老太还在,就前面那家。你要打听,问她去。”武老太。毅峰血液冷了一瞬。
看见武老太坐在牌桌前,背对着他。头发全白了,但骂人的嗓门依旧洪亮:“碰!
时间在那一刻凝固。她眯起眼,看了很久,忽然笑了,露出豁牙:“哟,这不是我家小宝吗?
出息了,穿西装了。”毅峰没说话。他看着这张脸,这张曾在他噩梦里出现过无数次的脸。
推他下坡时冰冷的眼神,祠堂里骂“祸胎”的嘴,雨夜里逃跑的背影。“回来干啥?
”武老太叼着烟,“要钱?没有。你爹妈早死外边了,我可没义务养你。”牌友们交换眼神,
起身想走。“都坐下。”毅峰开口,声音很平静,“我请各位阿姨听个故事。”他走进屋,
拉过椅子坐下,点了根烟。烟雾升起,他慢慢讲,从雨夜村长之死,讲到竹林遇袭,
武老太的烟烧到手指都没察觉。“所以,”毅峰弹弹烟灰,“我是来报恩的。武奶奶,
您当年推我那把,我没忘。您骂我祸胎,我没忘。您说爷爷奶奶不得好死,我也没忘。
“我就是告诉您一声,我回来了。以后您好好活着,长命百岁。我会常来看您的。”他起身,
身后传来武老太的尖叫:“你个杂种祸胎!你不得好死!”毅峰没回头。上车后,
他对司机说:“去东勒村。”“老板,那边路没修,车进不去。”“那就走进去。
”他需要看看村长的坟,看看那片竹林,看看自己是怎么从那里爬出来,一步步走到今天。
车窗外,稻田在夕阳下泛着金光,像十年前一样。只是那个被架在肩头的孩子,已经死了。
活下来的,是个满手鲜血的复仇者。---第五章 审判一、猎场曼谷,芭提雅庄园。
地下三层,手术室的无影灯亮得刺眼。马银川被绑在手术台上,麻醉剂让他眼皮沉重,
嫁妆120万妈妈叮嘱对外说8万,婚后一个月我傻眼了刘芳周浩全本完结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嫁妆120万妈妈叮嘱对外说8万,婚后一个月我傻眼了(刘芳周浩)/众享云霄
除夕直播我用玄学,他用科学,全网围观我俩破案(孙小雨陈序)完整版免费阅读_最新章节列表除夕直播我用玄学,他用科学,全网围观我俩破案(孙小雨陈序)/幸玛
狄公案·夜渡寒江(李元芳狄仁杰)最热门小说_全本完结小说狄公案·夜渡寒江(李元芳狄仁杰)/ice果
给大佬搓背搓成了他心上人陆昭陆总完结小说_完结版小说全文免费阅读给大佬搓背搓成了他心上人陆昭陆总/溪燃燃
朕登基那天,原配从城楼跳了下来(林蓁沈玦)最新小说_免费阅读完整版小说朕登基那天,原配从城楼跳了下来(林蓁沈玦)/泡芙和可乐
顾清然萧景恒《重生第十三次,我跪求庶妹当状元》完结版免费阅读_重生第十三次,我跪求庶妹当状元全文免费阅读/柑之如饴
沈糯糯沈暮云《当上后妈后我联合孩子整亲爹,怎么全家都慌了?》全本免费在线阅读_(沈糯糯沈暮云)最新章节在线阅读/柑之如饴
溪燃燃溪燃燃(因为怕死我成了死对头的小挂件)最新章节免费在线阅读_因为怕死我成了死对头的小挂件最新章节免费阅读/溪燃燃
流放路上我护他全族,回京那日他却告我父兄谋反(谢婉谢景行)全本免费完结小说_小说完结免费流放路上我护他全族,回京那日他却告我父兄谋反谢婉谢景行/亲爱的安小姐
渣男别走跑起来苏清清顾辰完结小说大全_免费热门小说渣男别走跑起来(苏清清顾辰)/迪托托